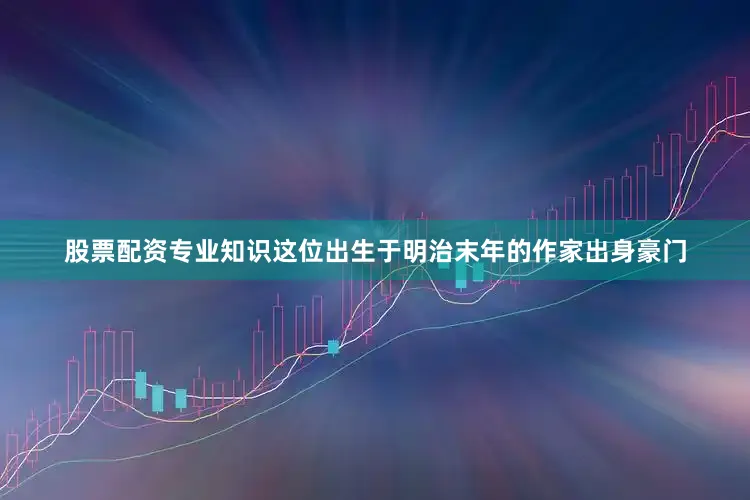
“此次日中战争,始于日军暗杀张作霖及对满洲的入侵。日军口称‘膺惩暴支’开始侵略中国领土。然而,困于长期战争,又改其名目为‘圣战’。这是毫无意义的辞句。欧洲战起以后,乘英军不振之际,日本政府跟随在德意旗帜下,图谋向南洋扩张。然而,此乃无智之军人及猛恶之武夫所图之业,非普通民众所好之事。政府有令,国民皆从。食南京大米未敢言任何不平,皆为恐怖所致。麻布联队叛乱之状,便是恐怖之后果也。今日打起忠孝的招牌,讨当今政府的欢心,为的是急于大捞一把。”
鲜有人能看穿军国主义浮光下的真实面孔。但永井荷风是少数从开始就看穿这副假面的人之一。1941年6月15日,当他写下这段文字时,心中深知自己头顶盘亘的是怎样磨牙嗜血的巨蟒——像他这样早负声望,著作等身的名作家,显然不会逃脱特高课政治警察的特殊关照。在过去的五年里,他已经多次婉拒了政府当局的利诱拉拢,这位以笔为生的作家宁可拮据过活,也不愿像他的同行那样,充当军国政府的笔杆子。日记,是他在这个高压时世中竭力保留的一方自由的净土,哪怕这方净土一旦被发现,自己难逃灭顶之灾——对暴横当道来说,他的名望是绝好的杀鸡儆猴的对象。
展开剩余93%永井荷风像。
为了守护这方自由的净土,在过去数年里,他“某夜深更而起,删去日记中不平愤慨之辞。又,外出之际将日记秘藏于鞋箱之中”。永井荷风之所以对自己的日记如此煞费苦心东匿西藏,是因为他早已见识过军国政府蹂躏思想的残暴手段。
“转向”
这一切可以追溯到1910年的“大逆事件”,明治政府以图谋暗杀天皇、制造暴乱的大逆罪名,逮捕了二十六人,其中就有著名的民权运动家幸德秋水,这位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也是最早的反战主义者,在日俄战争期间公开抨击日本的好战黩武的行径。大审院的审判完全是欲加之罪,所谓的谋逆罪只是对被捕者公开或私下谈话中只言片语的捕风捉影,暗杀天皇则从来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而他们真正的罪状,是所谓的颠覆性思想。最终,包括幸德秋水在内的二十四人被扣上逆贼的罪名,十二人被处决。死者的遗骸被从东京的不净门拉出,警察警告家属不得为自己的亲人修建坟墓、竖立墓碑。
在官方的鼓动下,社会给这些反战的社会主义者贴上了逆贼的标签,他们的家属受到牵连,其中一名遇害者高木显明的女儿只有六岁,却遭到社会的暴力围攻,“我晚上睡觉很害怕,夜里很黑,什么也看不见,有人扔拳头大小的石头,把玻璃窗都砸碎了,当时我想我大概要被杀了。在上学的学校里,也受到别人的言语欺负,我只好低着头,缩紧身子。在新宫街上,也可以听到‘逆徒的寺院’‘非国民’‘国贼’之类的恐怖的话语”。
“大逆事件”给永井荷风极大的刺激,同一年成立的“特别高等警察课”(特高课)将作家和“危险”书籍出版商列为缉拿对象。“危险”当然是一个宽泛的口袋,任何与日本当局有所颠覆的思想都可以被装进这个罪名进行缉拿。思想不屈服于真理,只能屈服于权力,那些悖逆的思想不仅要遭到缉拿,甚至连盛放思想的容器也会被砸烂。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悲惨遭际就是个令人骨战的案例,这位以小说《蟹工船》蜚声于世的作家,因为胆敢在作品中公开地抨击天皇而在1933年2月20日遭到特高课警察的逮捕,经过三个小时刑讯后,这位年轻的作家奄奄一息地倒在拘留室的地板上,抬到医院后不久就断了气。尽管特高课警察为了掩人耳目给遗体换上了新的线衫裤,对外宣称小林死于追捕奔逃导致的心脏麻痹。但当小林的家人朋友领回遗体进行清洗时,才看到他生前遭受了怎样的折磨:“脸孔苍白得可怕,凹凸不平的肌肉印下了剧烈痛苦的痕迹,这完全不是小林平时的神情;面颊凹陷,眼睛落了坑,左太阳穴上有一个铜子大的坑,四周还有五六块伤痕,因为皮下出血,都显得紫黑紫黑的。”
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
但最残忍的死因,却在他被刻意遮盖的下身,“从半覆着毛线围腰的小肚子直到左右两个膝盖,不管是小肚子还是臀部,前后左右,到处都染上了一层无法形容的阴惨惨的颜色,好像是把墨和赭红掺在一起乱涂上一般,大腿肿胀得好像要把皮肤崩裂似的”。
小林在狱中受到的拷打如此严酷,不得不让人想到特高课的警察乃是一群以折磨杀戮为乐的人皮怪物,这种残酷的虐杀行径,就像细线一样,一直连接到五年后在中国南京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小林这位左翼同志被迫害刑讯致死,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被他的左翼同志圣化为坚持政治信仰的不屈烈士,但比起他坚贞不屈的精神,恐怕给他的左翼同志最直接的震撼,还是他残酷的死法。20世纪30年代锒铛入狱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几乎在未经严刑拷打的情况下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宣布“转向”。日本左翼的两位领袖人物佐野学与锅山贞亲在狱中发表所谓的“转向”共同声明,他们撤回他们之前所有的主张:废除天皇制、民族的自治权等,转而投向天皇的怀抱,愿意为发展“日本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转向”成了当时日本知识界的流行词,《治安维持法》的修正公布后,特高课的思想警察着力于恩威并施的手段,根据一本“转向”技术手册的指导方法,“警察局局长应该从拘留所将被捕者叫到局长室,让他们坐在局长的椅子上,然后要自掏腰包叫来外送的亲子丼。所谓的‘亲子丼’,就是鸡蛋包裹鸡肉的盖饭,这样可以让人联想到亲子的关系。手册上还说,吃饭的时候,尽可能不要谈论政治思想之类的事,只能说些‘你的母亲很担心你’之类的话;而且不能多谈父亲,否则反而会造成学生对权威的反抗意识。”——对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转向”不仅廉价,也相当顺滑:只要把思想理念的效忠对象从遥远的莫斯科改换到近在咫尺的皇居宫城就可以了,至于像是打倒财阀资本和官僚,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对亚洲入侵的理念,完全可以和极右翼的国家社会主义理念无缝衔接在一起——极右翼的兴亚主义与之不谋而合。官方还为这些新转向的左翼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新舞台——“九一八事变”后粉墨登场的伪满洲国,他们大可以在这里建设理想中的“王道乐土”,把昔日抨击财阀和官僚的才华运用在歌颂伪满的城市建设和“日本拓殖者”在北方的荒原上艰苦创业的动人“伟业”上。过不了多久,这些昔日的左翼就会和他们当年的极右翼对手一起,在举灯摇旗的欢乐气氛中,携手合唱《啊!我们的满洲》。
浊流
永井荷风不属于左翼,也称不上那种敢于挺身对抗军国政府的勇士。这位出生于明治末年的作家出身豪门,少年时代游历美国、法国与中国,对法国唯美主义和中国的汉学都颇为推崇,他心目中的英雄是左拉,在法国德雷弗斯冤案发生时,这位法国大作家拍案而起,面对欧洲的反犹浪潮,为其辩护——尽管荷风深知,只有法国这样启蒙思想沐浴下的国度,才能容得下左拉这样敢于对抗社会的逆子,而日本,如前所述,那些抗争的逆子不是转向,就是被高压碾得粉碎。
荷风笔下的主角恰是这样的人物,他特别善于状写纤弱的个人是如何被社会集体压抑,虽然下场不是甘愿被社会抛弃,就是走上自戕之路,但只要能在压抑的浊流中保持内心坚定的自我,无论是放纵还是缄默,抑或死亡,这样的牺牲都值得。因为作家本人也如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纤弱多病,行走于背负着古老的负累却佯装昂扬走上“维新”之路的东京城中,总能精准地揪住那些为世人司空见惯却浑然不觉的压抑个体的扭曲现象,暗加讥讽。1929年2月11日的日记中,他注意到“青年团列队自幸边街蜿蜒至马场前门。前辈似的男子高举着或写有‘日本魂’或写有‘忠君爱国’的旗子”,这一现象让荷风敏感的心灵瞬间嗅出了不安的气味:
“近年来,此类游行大为流行,浮表上看似乎是国家主义极盛的表现,实则对于国家的基础日增危险。无论何事,假饰外表虚张声势,终会一败涂地。然而处身如此世间,不论何事,都动辄大喊‘忠君爱国’之类。治疗梅毒的广告中都大书爱国的文字。”
八年过去,这股所谓的爱国风潮在军国政府的推动下愈发炽盛,1932年4月9日,荷风点数了他迄今为止经历的历次战争:
“余熟忆往事,自日清战争以来,大凡每隔十年便有一战:即明治三十三年的义和团事件,明治三十七年、八年的日俄战争,大正九年的尼港事件,之后便是此番的满洲、上海之战。此战所唤起的民意沸腾竟胜过日俄战争之时。迎接军队凯旋的场面宛如祭典般热闹,如今日本举国上下似都沉醉于捷战的光荣之中。”
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驱使下,似乎在军事上接连不断地走向胜利,荷风看到的却是军国主义肆意横行下世风的一再堕落。他也逐渐体悟到了军国主义最凶险的本相,就是让军国思想像癌细胞一样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以爱国和胜利之名让民众成为军国主义自觉自愿的维护者。
悬挂国旗就是个典型的例子,1929年,街头还只是在庆典中才会悬挂国旗,但到1935年,永井荷风不得不到三越百货店花一元六角钱购买一面带竹竿的国旗,“我自从卖掉大久保的房子以后,至今还未悬挂过国旗,也未装饰过门松。然而,时闻近年来屡有壮汉闯入未悬挂国旗的人家施暴之事。为防万一而购太阳旗”——军国主义在一步步挤压日常生活的空间,消极的不服从已然无法坚守,在军国暴走突进的时代,唯有步追军国狂人的脚步,才能避免被狂人吞噬。到1937年,永井荷风悲哀地发现,军国主义已如附骨之疽,如此顽固地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之中,以至于深陷其中的日本民众已经习焉不察,在8月24日的日记中,他观察到“东京市民生活的样子,发现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似乎感到相对的满足与喜悦。对军国政治并没有感到不安,对战争也丝毫不觉得恐惧,毋宁说带着些喜悦”。
侵华日军士兵的“千人针”腰带,按照日本风俗,士兵出征前,其母亲或妻子、姐妹要为其制作一条布腰带,在街上找一千名妇女在腰带上面各绣一个小针包,每个小针包代表一个日本寺庙,战时系在腰上,以保佑平安,鼓舞士气。“千人针”腰带原本是为了表达对出征的亲人保命免灾的美好愿望,民间的这种风俗也从侧面反映了军国主义思潮在日本社会的泛滥。图片出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
军国主义真正恐怖之处正在于此,它会让人耽溺于战争之中,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更甚而言,生活与战争颠倒过来,生活成了战争的一部分。从孩童开始,军国政府就教育这些将来会被送上战场的新一代对战争脱敏。一篇小学四年级的课文标题是《制造大炮》,在制造大炮的科学性描述中,也会加入军国主义的譬喻,炮筒被反复地锻造、加热和冷却的过程,被引申为“我们的内心通过忍受冬季的寒冷和夏季的炎热而变得强大一样”——考虑到此时日本已经侵占中国东北炮制了傀儡政权,又发动太平洋战争,对南太平洋的诸岛开展攻势,这里冬季的寒冷和夏季的炎热所指为何不言自明。这篇课文特别提到为炮筒精心抹油的是“一名二十三岁的高中毕业生”——课堂里这些孩子的去处都已经规划得明明白白了。
人生成长的每一步都被安排了军事化的规训方式,在桥本一郎就读的中学里,校服就是军服,“我们和军人一样系绑腿,戴军帽,上课的时候,手持木枪跑步十公里,然后进行身体锻炼”,小学生会被教着把棍棒当成刀剑玩打仗游戏,而现在,发到这些中学生手中的木枪上安装的是货真价实的刺刀,在稻草人上练习刺枪。在一些学校里,稻草人上会画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面孔,“这可不是小孩子顽皮,他们是当真的”——对敌人的仇恨就这样通过军训教育的方式铭刻进了学生们纯真的头脑中。
这些教育当然不会仅仅靠说教、游戏和训练这些相对温和的方式达成,暴力是军国教育极为重要的一环。再没有什么比暴力更能体现出军国主义所尊崇的弱肉强食的绝对真理。长期在暴力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会相信世间的秩序是按照强弱来排列等级的——强大就可以打人,而弱小就要被打,弱者要服从强者,直到自己也可以成为去打人的强者。大忠野就是被打的那个人,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年他九岁,随着战事扩大,学校教育也变得愈发暴力,在一次课堂体罚中,老师下手太重,打残了他的一条胳膊,从此再也抬不起来,但学校里没人觉得老师做得不对,因为强者殴打弱者是天经地义的真理。
比起仇恨敌人,服从领导,更重要的是培养对死亡的崇拜,或者说是“牺牲”。对死亡的教育中包含了军国主义形态的三大核心:集体主义、绝对服从和个人崇拜。牺牲意味着消灭自我以成全集体,遵守命令战斗到死意味着绝对服从,而赴死的最崇高、最伟大的理由就是为天皇去死。尽管大忠野和同学们只是小学生,但老师和教官就已经拼命地把“战死沙场是我们的责任”的思想灌输进这些懵懂的脑袋:“他们告诉我们必须坚定、勇敢,心怀为天皇和国家而死的愿望,是无上的荣耀”。
“干掉他们,英美是我们的敌人!前进,一亿个火球!”
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永井荷风在电车上看到的这条战争口号,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是一句谶语,预言了这些被军国主义教育灌输的一代将会面临怎样的终局,他们也将成为口号中宣传的前进的“火球”。
神风特攻队,就是这些年轻的绚烂炮灰,在军国主义的蛊惑下,这些年轻人甘愿将自己塞进狭窄的战机座舱里,连同自己的身躯和三吨TNT炸药,一起化作货真价实的火球,冲向敌军的舰船。神风特攻队的制造商大西泷八郎宣称这是一种纯洁高贵的死法——“为国家和天皇献身,再没有比这更高尚的事业了。”
被拣选成为特攻队的队员大多是高校的大学生,他们并非头脑简单易被煽惑之辈,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饱读诗书,一位名叫佐佐木八郎的队员的阅读书单包括康德、叔本华、卢梭、穆勒、川端康成和谷崎润一郎。比起那些被单纯灌输为国献身理念的懵懂孩童,他对牺牲的思考显然更加深入,他之所以甘愿赴死,是因为他相信面对的敌人英美列强,正是旧资本主义的代表——当然日本同样也是,但他可以通过自己的牺牲,同时离弃和破坏双重枷锁,用自己纯洁的生命孤注一掷地毁灭,来换取一场注定的失败,那么,他将成为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军国主义当然可以披上崇高理想的绚烂外衣,就像那些转向的左翼分子在战时的殖民地为战争唱颂壮丽的颂歌一样,但当理想碰撞到真切硬实的现实时,所迸发出的并非绚烂的火花,而是一片不好清理的狼藉:“水手把来自几架攻击飞机的大片金属机身丢到海里后,开始用水柱冲洗甲板,水很快就被鲜血染红了。不久之后,甲板就清干净了”。
但在这些赴死的特攻队队员中,有一名队员却与众不同。他叫上原良司,他不是一位军国主义者,喜爱的读物是意大利史家克罗齐的《历史叙述的理论和历史》,比起那些为国家意识形态而赴死的同袍,他所期望的是用自己纯真的死亡,来唤起民众认清军国主义的真面目——看清这头蛊惑人心、吞噬人命的巨兽,在垂死挣扎前残害了多少年轻的生命和纯真的理想。在驾驶战机自杀式出击前夜,他写下了自己的遗书:
“自由是人的天性,消灭自由是有悖人性的,尽管自由遭到暂时的压迫,但经过持续的斗争必将最终胜利,意大利的克罗齐这句名言是我所抱持的真理。独裁专制可能一时得势,但终会覆亡,这是清晰的事实。在这场世界大战的轴心国身上,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法西斯意大利如何,纳粹德国又如何,眼下,独裁国家如大厦将倾。真理不仅在现实得到验证,也如历史揭示的那样,将会在未来继续证明自由的伟大……我的愿望是彻底的败亡,虽然作为人类群体中的一个国家的兴亡在事实上也是重大事件,但从整个宇宙来看,仍是小事。”
永井荷风如果知道有这样一位青年在遗书上写下这样的话,他或许会将他引为同调,就像他祈盼独裁专制的日本败亡一样,荷风也在日记中期盼与不义之国站在一起的军国日本,不亡待何。
上原良司给家人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战死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我所挚爱的人,我因着要去天国,不要进靖国神社。”
狂热的代价
“军国政府的暴横愈演愈烈,社会终将发生巨变……但不管当权者如何暴恶,都无法束缚心灵的自由,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自由。”
诚如永井荷风的这句箴言,唯有实实在在的生活,唯有真真切切的生命,才是平凡如你我一般的庶民大众,抵御军国主义狂风暴雨的港湾,因为切实的生活容不下虚假的口号,充实的生命也容不下虚伪的真理,生活不能将匮乏当作富足,生命也不能将毁灭当作生存。
军国主义最具煽惑的力量,便是将民众的目光从生活中吸引开来,用意识形态的口号来诱骗人们踏上仇恨与狂热的泥淖。它会将战争的毁灭粉饰为创造的伟力,会用所谓精神的富足来掩饰物质的匮乏,会用战争弱肉强食的谬论遮蔽生活互助共存的真理,它让人相信周遭都是窥伺侵略自己的仇敌,挑起纷争与不和,用以掩盖内部的动荡与不安,它宣称追求的是“亚洲和平之道”,但带来的却是遍地残垣、生灵涂炭。
从某种程度上说,军国主义的信徒也背叛了生活,他们如此狂热地将自己的生活献祭给战争的巨兽,作为启动它肆虐暴行的食粮,驾驭着这头巨兽去毁灭他人的生活、蹂躏他人的生命,那么,将这些狂热信徒引向正途的最佳方式,或许就是也让他们饱尝生活与生命遭受毁灭的苦痛。
1945年3月9日,载有总重量达2000吨燃烧弹的334架B29型战机飞临东京的下町,实施轰炸。经过两个半小时的东京大轰炸,在40平方公里内的25万户居民房屋被毁,数百万人失去家园,10余万人的生命被夺走。轰炸是如此惨烈,一位幸存者在一座看起来是小巷的地方,发现了一具异样的尸体,“头发烧焦了,衣物烧毁了,烧焦的皮肤裸露着。除了那些被压在倒塌房屋下的尸体外,其余尸体有的匍匐着,有的横卧着、有的仰着,而只有这一具尸体的脸是冲着地面蜷伏的——那是一位抱着婴儿的母亲,她在地上用手挖了一个坑,十个指头沾满了血污,指甲一个也没有了。大概感觉自己不行了,就用手指挖开坚硬的地面,放下婴儿,自己覆盖在上面隔离火焰,希望保护自己的孩子生命。婴儿的衣裳一点也没有烧着,一双可爱的小手还抱着母亲的一只乳房,但由于烟熏,孩子也已经停止了呼吸。”
永井荷风也在轰炸中失去了他心爱的书斋“偏奇馆”,靠着侥幸才只身从轰炸中逃出生天,当他踉跄来到老友家求助时,形单影只,只剩手中的那件包裹。积年来的藏书与珍藏全部都灰飞烟灭。但他并没有丝毫怨言,却将美军的轰炸称为“天罚”,他只是感慨这天罚为何来得如此之晚。
1945年8月15日,中午,沙哑、低沉、模糊的声音,穿透窒闷的夏日暑气,从收音机里传出来,上亿日本人都听到了这个陌生的声音——天皇的“玉音放送”。这是过去的20年里,日本的臣民第一次听到他们最高统治者的声音。在以往,尽管天皇的“御真影”被悬挂在每一间办公室、每一座学校、每一座工厂里,每个人都将天皇的《教育敕语》铭记于心,但没有任何一个普通臣民聆听过天皇的声音。他们唯一熟悉的是服从,无条件地服从那个镶在镜框中、身着戎装的“现人神”的旨意,但此刻,这个声音却发出旨意,告诉他们战争结束了。已经回不去的家,已经无法重见的战前生活,已经崩塌颓废的道德体系,还有那个曾令上亿日本人真诚相信“大日本帝国”的幻象,如今都在烈日炎炎下熔化了,昔日被献祭给军国主义的生活,终于被吐了出来,但只是一地狼藉的废墟。
泪水、沉默、不甘,以及松了口气,在那漫长的一天结束时,每个人都要以各自的方式与过去说告别——或者用即将到来的新时髦话语,说“Goodbye”。
对永井荷风来说,这是多年来他最欢欣的一天,尽管几乎失去了全部财产,尽管战时的压抑和匮乏戕害了他本已病弱的身体,让他的胃病更加严重,但他依然请染坊的阿婆弄来鸡肉和红酒,与好友召开庆祝欢宴,直到酩酊大醉。在这天的日记中,他用墨书写道:
“正午停战”。
战争终于结束,和平终于到来,无论是自愿还是强加,战后废墟上的日本宣称要建立一个反战的和平国度。但和平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反战又该如何解释?是反对那场给亚洲各国带来苦痛的侵略战争,还是反对所谓打了一场明知会输的战争?和平是因为自己遭受了轰炸的战祸,因惧怕战争的灾祸而将和平当作庇护所;还是认清自己作为战争侵略者的罪行,用真诚和友善治愈战争带来的创伤?
两个是之间的差异,或许大于是与非之间的差异。但有一点却确定无疑,谎言总会戳穿,罪行也总会见光,因为历史的因果之网如此连绵而细密,那些自以为可以逃脱隐匿的罪行,终会被它一网捞起,大白于天下,于是那些罪行与谎言,都将在审判台上受到应有的惩罚。就像永井荷风在战后所写下的那句话:
“想想我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吧,这是报应。”
作者/李夏恩
编辑/罗东 李永博 申璐
校对/薛京宁
发布于:北京市广东配资炒股,股票炒股配资开户,在线炒股配资服务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